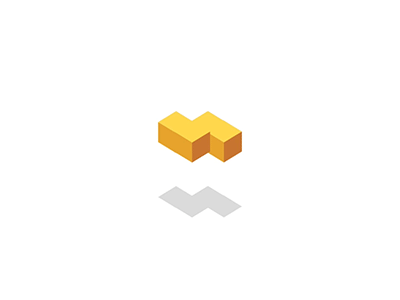认真对待民法中的身份 认真对待民法中的身份 认真对待民法中的身份 更多精品文 章来 源自 教 育 网
关键词: 身份;民法体系;伦理秩序
内容提要: 当今的私法研究以财产私法为重,而身份私法相对薄弱。身份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式微源于学界对身份法的历史偏见、财产法优位主义以及民事立法理念的片面继受等因素。民法体系的逻辑完足、民法典的最终成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现实对身份利益保护与救济的需求,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民法领域的身份问题。身份法研究既要追求身份关系的制度构建与伦理秩序原理间的协调与平衡,又应致力于身份制度与民法整体制度的逻辑融合,还要为现代亲属身份生活领域的利益纠纷化解提供理论基础。
一、引言
“身份”作为主体在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或资格,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每个社会个体或组织体都会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身份、身份关系无处不在。政治国家需要藉由身份关系来组织管理社会、谋求社会秩序,譬如公务员制度、户籍制度、身份证制度的功能意义。而且,有时一个主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还关涉其资源的占有份额、利益的分配依据,诸如财产继承制度、薪金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而且,无论社会形态发生怎样的变迁或更迭,身份在伦理秩序领域的存在意义始终未曾缺失过。梅因所谓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1]96-97只揭示了个体的法律人格和社会地位从古代到近代发生革命性转变,但梅因的断言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消亡(注:有教科书在介绍梅因这一断言时认为,“这显然是对人类发展史的曲解”。参见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二、身份法研究之现状解析:观念变革与法律继受 (一)身份法研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法制史上身份法的封建糟粕导致现代民法学研究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在古代西方社会未曾从“身份”进步到“契约”之前,身份法的地位在法制史上优于财产法。众所周知,早期的罗马社会基本就是身份社会,罗马法的人法就是“身份法”,它担负着社会组织化的功能。[5]罗马法的人法实质上是一种人格法,其有关自然人身份的规则确定了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作为组织身份社会的基本法,具有公法的性质。而财产法不过是身份法的附属品,即身份确定是财产分配的前提,无身份即无人格;无人格即无财产。[6]罗马法将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身份“捆绑”在一起,统治者利用这一法律工具(亦可谓之政治工具)对被统治者进行“适格”判断,实现其统治所需的差序格局;更有甚者,罗马法将奴隶排除在人格判断之外,使之成为法律的“客体”。罗马法的身份人格显示出其反伦理性,也因此招致后世诟病。[7]等级森严的身份法建立后,社会财产的分配与经济利益的流动自然就以此为标准和依据。身份的高下,意味着人格的优劣、财产的多寡。直至中世纪,身份法仍归属于公法、社会组织法。中世纪的身份权是人身支配权、是专制权、是绝对权。身份社会几乎就是“封建社会”的别名!击碎身份社会的枷锁遂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于是在法律领域,从身份法到契约法的转变,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二)身份的民法学意义被遮蔽
现代社会中,“身份”的政治学意义、社会学意义湮灭了其法律学意义。在多数学者们的意识领域里,身份问题是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命题。法学理论研究者多认为身份问题似乎不属于法律、尤其不是民法学研究的问题。政治学学者热衷于研究“公民身份”,认为公民身份比起其他各种社会身份,更能够满足人类的根本政治需求。[9]7公民身份由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所组成,三种要素分别表明了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三种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0]代译序。社会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社会哲学等角度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展开研究,认为社会整合是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身份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社会身份是基于具体个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形成的身份,个体的社会角色成为其各种责任担当的依据。[11]3政治学、社会学对“身份”问题给予了热切而深入的关注。相形之下,私法学领域的“身份”问题似乎无足轻重,进而“身份私法”的研究也似乎无所必要。然而,身份问题不是专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的领地,民法学在身份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民事生活领域中的婚姻家庭制度、知识产权制度、行为能力制度等都涉及个体的身份问题,其间主体的诸多身份利益都需要民法的关怀。
在涤除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身份”的糟粕意义后,现代身份法存在的意义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只不过现代社会中,法律将承担社会组织管理与弱者保护功能的身份法主要交给公法规制(如宪法、行政法、新兴的社会法及一些特别法);而仅仅将婚姻家庭领域的身份法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即狭义的身份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学领域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学领域的身份问题应有适当的界分,扩大化地理解私领域的“身份”可能也会弱化甚至遮蔽民法上的身份法特质。有民法学者基于近代社会契约与身份同时勃兴,大量的身份契约出现在新兴社团组织关系之中,个体通过契约重新组合,进入新的身份体,认为私人间法律关系的一些领域越来越多地通过身份关系来确定。[12]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诸多新型身份体更确切地说是社会身份,而非严格意义的“私法”身份,它最多也只是现代民法社会化在主体制度上的体现。将民法视野中的“身份”社会化、一般化而交由私法调整,实乃民法(私法)不能承受之重!
(三)身份法研究遭受财产优位主义的干扰
民法的财产优位主义导致了学界对身份法研究的轻视。从发生学角度看,古代社会身份法既先于财产法,又优于财产法。从调整领域观察,古代社会身份法一般与财产法混同交织,并未俨然界分。但是近代以后,随着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法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是从物质基础上破除旧制度,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彰显物文主义(即“所